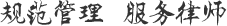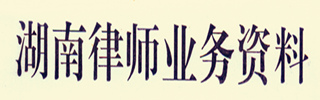张献 周晨曦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10月2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其官网发布《关于<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将《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在互联网上进行了公开。该办法是以2014年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交易管理办法》为蓝本修订而成。
近年来,随着我国互联网普及程度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电子商务成交量迈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我国的网站数量为523.36万个,网页数量为28162240.6个,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了59.6%。在此基础上,根据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年全球电子商务数据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的电子商务交易额总数为47311亿美元,其中网络交易零售总额13095亿美元。然而,高速增长的互联网交易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和不足,比如因欺诈或不诚信交易而引发大量的互联网诉讼、电商平台跑路等,加强对我国网络交易的监督、不断规范我国的网络交易环境势在必行。从《网络交易管理办法》到《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突出了监督的作用,正如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所指出的:基于市场监管职能,力求网络交易市场监管执法全覆盖、一体化…旨在进一步完善网络交易监管规制体系,同时又必须对一线监管工作中的可操作性予以充分考量。
监督管理,从法的价值层面上讲,隶属于法的秩序价值。正如博登海默在《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所称:法律的许多制度都旨在跋扈权利和预期安全,使它们免受各种强力的侵扰,这些强力常常以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利益为由而试图削弱法律结构的完整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法律就必须能够抑制住政治压力或经济压力的冲击。
纵观《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尽管对于网络交易秩序的完善较之以往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笔者认为仍有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明确。
二、以“诚信”作为网络交易监督体系的建构基点
市场竞争的发展已进入经济学家推崇的“凸性组合”时代,即以政府干预之长来弥补市场调节之短,以市场调节之长克服政府干预之短,从而实现两者的最优组合。众所周知,市场调节之短主要来源于信息不对称和不诚信经营。作为市场经济的天然属于,信息不对称难以切实克服,而不诚信经营作为破坏市场经济有效性的重要因子,则可以通过合理有效的市场监管法律体系予以有效的规制。在《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应当从网络交易经营者、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和监督管理三个层面加强对市场诚信的监管。
(一)应当将个人信用信息与网络交易经营者资质挂钩
从现有规定来看,在网络交易经营者登记申请程序中,申请者的个人征信并不属于必要的审查条件。换言之,无论申请者是否有失信行为均不会阻却其成为网络交易经营者。首先,网络交易与传统交易的区别在于买受人和出卖人是在网络上发生的交易往来,彼此之间并不知悉,甚至素昧平生、相隔万里。如果不将个人征信作为成为网络交易经营者的前置条件,那么无疑将可能加剧了买受人的交易风险。其次,网络交易经营者的不诚信经营行为也应当与个人信用信息挂钩。《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12条规定了9种不诚信经营的方式,但是除了承担必要的民事和行政责任外,现有的征求意见稿并未建立必要的信用风险警示体系,如果能在现有法律责任之外构建一套信用风险警示体系,即参照当前个人征信登记系统的机制对网络交易经营者的不诚信经营行为予以登记并公示,对于督促网络交易经营者规范经营无疑将极具裨益。最后,将个人信用信息与网络交易经营者挂钩也是促进解决执行难的有效手段。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切实解决执行难”的部署,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3月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6年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体系。在网络交易中,一旦经营者因个人失信行为被纳入失信人系统,如果能将此作为限制其获取网络交易经营者资质的条件,对于督促其履行相关义务无疑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充分利用其“软法”建构和实施能力对网络交易经营者的诚信经营进行监管
所谓“软法”,有学者认为是指那些效力结构未必完整、无需依靠国家强制保障实施、但能够产生社会实效的法律规范。基于我国近年来网络交易乱象丛生的状态,有学者提出了“软法先行,硬法托底,刚柔相济,混合为治”的网络治理模式,即充分发挥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的监管作用,提高对网络交易经营者的监管能力。
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作为经营者所依托的“虚拟市场”,在为经营者提供交易场所前势必会对经营者进行必要的资质审查,包括身份、经营场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类型等。从信息获取的便利性角度出发,赋予其必要的监管职能是完全可行的。另一方面,基于责权利平等的基本理念,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也必须在其平台内部建立系统、全面的监管规则和监管实施部门,对在平台上经营的主体存在不诚信经营的行为进行监察和及时有效的处理。
据此,笔者建议《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在现有的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警示机制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就经营者不诚信经营行为的监察义务和失察情形下的法律责任。具体言之,可要求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在授予经营者入驻许可前对经营者身份、经营场地等进行审查,同时建立抽查和长效巡察机制,对实际经营者与登记经营者不一致、登记经营场地不实等涉及经营者诚信经营问题等因素进行检察,如果消费者与网络交易经营者产生纠纷,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能有效提供经营者信息(包括身份信息、经营地址等),那么消费者有权要求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据此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三)市场监督职能部门应不断强化“监”的功能
从文字表述上,我们习惯于强调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职能,但事实上,“监”和“管”并不是相互重复的语义,“监”突出的是事前的防范,而“管”则更着重于事后的救济。从网络交易监督的执法重点来看,“监”的重要性应当更大于“管”。“监”到位,意味着将对潜在的网络交易违法行为产生足够的威慑力,迫使其规范经营并最终从达到净化网络交易整体环境的作用。同时,“监”的加强,也会有助于职能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减小“管”的压力,从而能够调配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来反作用于“监”的发展。
从当前公布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来看,目前着重突出的还是强调市场监督部门“管”的特性,并且并没有赋予其必要的履行“监”的权限,在“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原则影响下,对于市场监督部门开展网络交易违法预防性措施无疑产生了利空的影响。因此,笔者建议在《办法》的“监督管理”部分,进一步赋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使“监”的功能的权限,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有权对辖区内的网络交易经营者、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合法经营等事项进行监督管理,并对相关违法行为及时依权限进行处理。监督管理的方式可以采用抽样调查、暗访等方式开展,同时也可以通过向消费者发放问卷调查或在其官方网站设置消费者反馈板块,及时听取消费者的意见并据此进行有针对性的执法和防控。
三、结语
如前所述,网络交易由于背离了传统的面对面特性,发生诚信风险的可能性会大于传统交易。为此,在网络交易中,对于网络交易经营者的信用要求应当严于传统的线下交易模式。同时,为了督促网络交易经营者的诚信行为,必须加重网络交易平台的监督责任,促使其成为网络交易监督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最后,进一步强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风险预防职能,对于净化网络交易市场环境也是重要的环节。